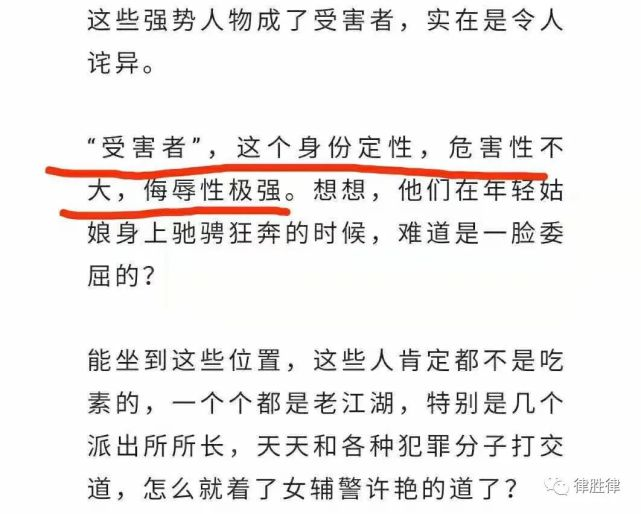(一)
该案的裁判文书早在撤回公开之前已经看过,本不想参议。但因为职业圈子原因,不幸看到不少对该案的声援,认为许某蒙冤、无罪。阅后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。
随便截图几幅如下:
既有人们灵感百出的脑补、臆测,却也不乏部分法律同仁们草率地信口开河,甚至有人上纲上线到耸人听闻的“政治错误”。
(二)
愤怒源自偏见。
愤怒的草芥用不乏恶意的推测主动捏造事实、添加情节,创造一个真假混杂的新案件,满足其想象中故事,群起攻之,众口铄金。
公安局副局长等公职人员是被害人?
法律平等保护任何公民,无论其是皇亲国戚还是草芥贫民,法律无需以无视公职人员保护的方式强调其亲民。
官员白嫖(或白睡)临时工?
既然案件性关系没有违背许某意愿的事实,自愿的不正当性关系却冠以“白嫖”是否存在双标问题?即一般平民间的不正当性关系不属于“白嫖”,仅是违背道德的行为,而涉及官员的不正当性关系则属于“白嫖”,不但违背道德,还违背契约,拒绝支付债务。
我认为这“白嫖”已经滥用,已对人不对事,因人而定。这是把女性权利在性领域的进行物化,赤裸裸的性别歧视,侵害了女性在不正当性关系中仍然作为一个人的应有尊严。
官员遭受敲诈勒索不及时报警是纵容犯罪?
可以明确,官员作为被害人角色的时候,是否控告犯罪是其个人权利而不是义务,没有义务告发(除非涉及国家安全、社会公共利益等时,可以存在例外)。
警察因为其本身打击犯罪职责,对于他人遭受侵害的罪行是有告发、打击的职务要求的,但当警察自己成为被害人时,警察有权盘衡利弊,对控告权作出适当处分,就如同抛弃自己的财物那样,无可厚非。
至于“政治错误”之论,算了吧。可能案件本身就问题不大,而且也无需动辄上纲上线,随便扣上一顶“政治”的帽子。
以上这种种谬论,归根到底是人心中的魔鬼在作祟,魔鬼就是人心中已被黑化的警察形象、官员形象,愤怒源自这样的狭隘的、暴戾的偏见。
(三)
民粹的狂欢、戏虐代表群体的不理性抗议和宣泄,尽可一笑置之。但部分法律同仁参杂其中,信口开河,同样令人叹为观止。
有同仁认为一,该案许某索财系事出有因,基于此不能评价为刑事上的“非法占有目的”,此言差矣,系得其一不得其二。
确实,事出有因的索财并不一概而论定为非法占有为目的。为索取合法债务,不当使用了要挟办法的,而且索取的财物也不是和应得金额差距太大(过度索赔,因案具体而定),一般不认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。
但如果索取的财物或债务不是法定允许的或协议约定的,通常是倾向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。
公开的判决书可以找到两个事实依据支持认定该案索财具备“非法占有目的”:
其一,许某在时跨五年期间,通过相同的作案套路,先与不同被害人发生性关系,后以自己家人要闹事、告发等理由,抓住被害人害怕曝光、影响工作、家庭、名誉的心理软肋,索要9名被害人财物三百余万元。
俗话说“吃一堑,长一智。”如果要说许某在案中和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是情之所至,为感情纠葛而索取财物,不存在其他目的的话,那么经历第一次、第二次感情失败,许某应当知道以发生性关系为办法,追求一个人或维持一段感情是不切实际的,应该停止。
但一而再,再而三,在短短的五年间,前后九人十次,以同样的套路,取得款项三百万,这不符合男女谈情论爱的常情表现。
其二,许某案中交出财物的被害人无一例外,均是警察或工会主席、校长、卫生院工作人员等吃“铁饭碗”的公职人员。
这些公职人员有固定稳定不菲的收入,但又有组织清规戒条约束,涉及丑闻往往顾虑重重,害怕声扬曝光,大多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甚至愿意花钱消灾。
这样的一种群体对象恰恰和那种持“要钱没有,要命一条。”或“无所谓、爱咋咋地”处事态度的群体形成对比,这显示许某在案中对涉案对象的物色、选择上是经过深思熟虑、精心谋划的,并非纯粹的一种谈情论爱目的。
许某和涉案对象发生性关系并非出于衷,动于情,而是一种动机不纯的物质驱动。
以上一二,可以综合认为,许某在该案不是一个情感羞涩的傻白甜,而是一个食髓知味的、危险的桃色陷阱设计师,可以设计出一种以发生性关系为铺垫,最终索取非法财物回报的局,并反复实施使用,非法获利。其索财行为具有主观上的“非法占有目的”。
有同仁认为二,鉴于性关系的存在,相对方应当有所表示(物质回馈)。许某索要的是应当得到的,什么理由和借口,无关要紧。我认为很离谱。
把性关系和物质回报直接划上等于号,是否等同于性关系可以物质购买(婚姻关系、强奸索赔等除外)?
且不说法律对卖淫嫖娼的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规定,即使在民事领域也大概未曾见过支持、允许性交易、性报答的规定和案例。诸如基于解除非法同居关系请求青春损失费的、基于婚外情赠与关系请求履行给付的,实乏见立法、执法给予肯定。
此说不但无法寻求法律的支持,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睽睽相违。或许,二审裁判会在裁判文书中执行(法[2021]21号)文的要求,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加强文书释法说理。
(四)
案件裁判揭示的险恶在许某身上而不是警察、公职人员身上,案件舆情映射出的荒诞在民粹而不是司法。
不排除在不正当性关系中,一方可以获得另一方的补偿,但这种情形以给付方在意志充分自由的前提下,心甘情愿给付为限。
从当事人角度,大体可区分为两种:其一,一方以请求形式,不夹杂任何威胁、要挟内容,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、善后、扶助等名义款项,给付方自愿给付的;其二,一方没有向给付方主张请求给付,另一方主动自愿给付款项的。
部分同仁的认识断不了屁股决定立场,利益主宰理智的病根。
明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以威胁、要挟办法,强行索取一定数额财物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,为何要断章取义,割裂事实,片面强调性关系的道德问题、性关系的损失补偿合理问题等,无视取得财物是通过以家人闹事、身败名裂后果相要挟的手段,更无视精心设局、反复实施牟利的非法动机,到底何故?
这里面存在理解和认识的分歧问题,属实,可求同存异。
但不排除部分人刻意曲解法律,有籍机扬帆万里,乘风破浪,通江达海,一逞声名的小算盘。也不排除部分人系耽于谣传的漂亮女孩图片,勾动六根之火,而蠢蠢欲动,以致放浪形骸,大放阙词。
这到底是民粹的狂欢还是职业的沦丧?
(五)
虽然定罪无疑,但法院的裁判也确实存在问题,不一而尽。
其一,在事实认定部分。
指控的第4起陈某甲10.8万、第8起林某14万和第9起108万,此三起涉罪事实在判决书里没有认定通过要挟、威胁办法索取财物,不符敲诈勒索犯罪构成,裁判犯罪依据不足。
这应是二审裁判需要查明的部分,也是许某罪轻辩护的入手之一。
其二,在量刑方面。
罚金500万元虽然符合刑法规定,但许某不是公司企业,也不是经济能人,能否履行如此巨额罚金值得怀疑。
要知道其退赃尚且不足,仅退得五十万元,无法悉数执行该案罚金岂不自损司法权威?司法解释已基于执行难的问题,主动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删减了死亡赔偿金、伤残赔偿金,在此背景下,一审裁判巨额罚金应该三思。
其三,对赃款的处理。刑法规定,被告人违法所得,应予追缴或退赔。
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,应当及时返还。但一审裁判判决追缴被告人许某违法所得370余万,这意味370万元不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,与裁判定性相悖。
既然属于敲诈勒索案件,理应将370余万元返还九位被害人。如果返还给九位被害人(公职人员)的款项存在合法性问题(贪污受贿?巨额财产来源不明?甚至在许某进入公安部门工作过程中有否违规违法?),完全可以另案处理,交由纪委监察委调查、立案处理。
其四,一审裁判文书上网后又突然撤下,有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之嫌。
裁判文书上网规定,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,应当在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在互联网公布。依法提起抗诉或者上诉的一审判决书、裁定书,应当在二审裁判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在互联网公布。
文书上网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,上述规定是强调文书生效后七日内上网的硬性规定,但规定没有禁止未生效文书不得上网(不得上网的文书主要为国家秘密、未成年人犯罪等等),也即未生效文书是否上网可由裁判法院具体裁量。
该案一审裁判文书未生效即公开并不违反规定,但既然已经公开,却在舆情鼎沸之下匆匆撤下,显为定力不足,授人予柄。
其五,据传,二审许某家属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后遭致二审法院拒绝,理由为已经由官方指派法律援助律师。
最高院适用《刑事诉讼法》解释第51条规定,对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,被告人的监护人、近亲属又代为委托辩护人的,应当听取被告人意见,由其确定辩护人人选。
该案二审指定辩护人是否经许某同意并排除其近亲属委托律师,是否如同劳荣枝案指定辩护那样招致非议?这不应仅仅是一个口头通知或答复。
要平息家属质疑和愤怒,需要专门安排家属委托律师会见许某,核实其真实委托意愿。仅仅是核实委托意愿的会见,可以限定时间会见,可以安排监督,防止案情交流。